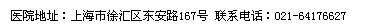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急性淋巴管炎 > 淋巴管炎治疗 > 这家伙生于60年代34nbsp冇
这家伙生于60年代34nbsp冇
我像一只沉默的土狗,闻遍了严塆每一个角落。——题记
(封面插图:《严肃作文》御用涂鸦师、大学同学邱赛强)
所谓“双抢”,就是抢割早稻、抢插晚稻。
“双抢”是每年必经的农事,时间在7月中下旬。对农民来说,就是一场鏖战。
当年“双抢”,最著名的革命生产口号是:“不插‘八一’秧!”指的是,晚稻必须在每年的8月1日前插完。
一
几次在“双抢”前,听到别的塆的凶信——又是哪个塆哪个塆,又有几个女伢,相邀“跳塘了”。
跳塘,就是投塘自尽,是“跳水”的统称。
老家浠水,丘陵地带,河、水库、干渠、湖,都有,应该跳什么自尽的都有。也许塘最多,又近在塆里塆外,选择跳塘的多些,所以统称“跳塘”。没听说过有男伢跳塘的。传出来的消息,多是女伢。
凶信的情节,大抵如此:
初中生尤其是高中生,一毕业,马上正面遭遇“双抢”。几个玩的合适的,相邀结伴,跑到省城武汉玩两三天,回家后,就相邀结伴,跳塘自尽。
有说,跳塘时,互相手拉着手的,也有说,一起牵一根麻绳下水。
多是十五六岁到十七八岁的姑娘伢,一般都搞过五六年、七八年的“双抢”。
她们以这种平静而惨烈的方式,拒绝即将到来的生命中最后的“双抢”。
应该家庭成分各不相同,但一定是,家里没有人在城里工作吃商品粮,也没有人在公社,在大队,哪怕是在生产队当干部,完全没有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她们知道,大城市偶尔的招工,当兵,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和自己无缘。
而前面的路,就是嫁到几里外的某个塆,生好几个伢,搞很多的“双抢”,生老病死,终其一生。
小学的几个同学,证实我当年听到的消息不假。
比如严塆的更北边、豹龙庙的北边,一个叫大灵的公社,就有这种惨剧。大灵那边,山多,也高一些,应该比我们曙光大队资源更少,也更穷。
还有同学说,高潮大队也有跳塘的事。高潮的穷我知道。我外公外婆舅舅家在高潮大队一队,那些年,一个工分的分值,一直只有2分多钱。
除了跳塘,还有上吊、喝农药的。那时候的农药,有六六粉和敌敌畏,致命的是“敌敌畏”。
当年夭折的少女,还有一类,就是情窦初开两情相悦,不小心怀上了,消息泄露,没脸见人,选择跳塘。也有玩的合适的女伢(现在叫闺蜜),情绪感染,怀着“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义气,陪同跳塘的。
(挑稻谷)
二
跳塘、上吊、喝敌敌畏的,毕竟是极少数。活着的人还有继续活着,在每年的“双抢”,经历各种遭遇,习以为常,无力在意。
整个“双抢”期间,太阳是最大的。山蚱子和“歌乐”(两种“知了”)不停的聒噪,使天更热,人心更烦。除了蝉蜕可以捡来卖钱,至今对蝉没有好印象,对“蝉鸣”的诗意表达无感。
草帽、斗笠和长袖上衣,是必备的。而降温和防暑,一是茶水,二是绿豆汤,三是“人丹”“十滴水”。
茶水,是自家人送到田边,或者生产队在稻场烧一大壶送来。都是普通的绿茶。茶叶一般来自林场,林场有茶树林,多少钱一斤不记得,都是自家铁锅炒制、晾晒而成。
经常打夜工,有时候有“双抢饭”吃,不要钱。放夜工了,去稻场,端着品碗蹲在地上,吃几碗干饭,甚至糯米。
人丹和十滴水,是当年唯二的防暑药品。是生产队发放还是自己买,不记得。人丹口服,除了粘在舌头上,把舌头染红,感觉不适,还算好。十滴水,黑,浑,苦。
屋外的地面滚烫,赤脚行走,不能脚踏实地,更不能稍有站立,要快速地小跳,利用离地的瞬间,避免烫伤。
下田大多是赤脚,干活儿方便。家境好一些的家庭,有深筒子胶鞋,也叫“筒子鞋”,决不是每人都有。一般是干活最多的壮劳力,和身体不好或者正在生理期的女人用。小孩没事,晴天穿出去显摆,会被大人打骂。
露在外面的皮肤,晒的漆黑很正常,长几身痱子、脱几层皮、被蚊虫咬一头的包,都很正常。
扯秧、插秧、割谷、挑草头,总会遇上水蚂蟥,尤其是扯秧坐在田里的时间稍长。发现时,一般已经流血。啪一巴掌,下不来,扯一把,手指捻个半死丢了。小孩觉得不解气,找根细树枝把蚂蟥贯通(有点像莫言写的《檀香刑》),通体翻转过来。有火柴时,还会点火烧,看蚂蟥缩成一团。
蛇也经常遇到,不知道哪些蛇有毒,也不确定塆里有谁被咬过,但一律都很吓人。常见的有花蛇、土地蛇、水蛇,抱谷的时候,甚至会抱到一条什么蛇。扁头蛇(应该是眼镜蛇)也有,在路上或者屋前坪子,盘成一个大饼,高昂着头,一动不动,大大咧咧地晒太阳。
对付各种虫子的袭扰,就用草帽驱赶,或者巴掌怕打。有种叫“绿虻”的家伙,比苍蝇大几倍,头部放绿色,看着恶心,被咬了十分痛痒。跟欺负牛的牛虻,估计同宗。
比较恐怖的是,身上长包,脓包。常见的部位,是大胯(大腿)、屁股、头上、脸上。基本不予理睬,尤其没钱的人家,任其生长,直到成熟、化脓、穿孔,等着自愈。
开始时,一个小红结节,然后逐渐长大。熟透了、穿孔前,里面充满了脓液,鼓起充分,表皮薄亮,有节律地掣动,痛苦不堪。特别在夜里,痛的无法睡眠,嘴里发出“咝~”声,又不敢碰,只好冲它吹气,稍作缓解。一朝突然穿孔,脓液尽出,恶臭难闻,创口处慢慢地瘪下去,有难看的褶皱。
年年长包。我记得去三店卫生院割过一次包,长在脸上的。医生割一个口子,也不打麻药,一根棉线捻子,手指搓转着深入,吸出脓液,拽出来。如是者再。好在小,恢复的快,居然不留疤痕。
手指头、脚趾、脚底、脚背,也经常莫名地红肿,痛痒难受,也是任其消长。尤其手指头,化脓,情形一如脓包,指甲会因此松动或脱落。
极少有人因此送院治疗。不知病因,老家人统一俗称“痋了”,叫“脚痋了”、“手痋了”,一律归咎于毒辣的太阳和各种无名的虫豸。毒辣的太阳暴晒,烤炙泥土,毒害身体发肤尤其是赤脚;而无名的虫豸,阴谋噬咬。
Chong,是读音,不知何字,姑且用“痋”。痋网上说,痋,有关“病”,有关“虫”。痋,多音字,读téng或chóng,音为téng时,意思古同疼,如寒热酸痋。音为chóng时,动病也。
还有“痋人”、“痋术”之说。“痋人”指一种身体特征酷似于人类的大虫,身体肥硕,蠕动爬行。痋术是一种巫术,痋术、蛊毒和降头并称滇南三大邪法。曾盛行于东南亚一带。在我国云南似乎还有人使用。三者皆是利用自然界的某些虫类将人置于死地的法术。
脓包是“身体某部组织化脓时因脓液积聚而形成的隆起”,皮肤软组织感染,包括毛囊炎、疖、痈、淋巴管炎、急性蜂窝组织炎及褥疮感染等。
说是由于细菌侵入人体皮肤而发生的炎症反应,局部可出现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严重时细菌及毒素进入血液循环可引起毒血症或败血症,伤口感染是细菌在体内大量繁殖的结果,脓是机体组织炎症过程中形成的浓稠或稀薄的渗出物,其中包含变性、坏死的白细胞、细菌、坏死组织碎片和渗出的组织液。
(传说的“痋人”)
三
比较恐怖的还有,大太阳底下干活儿,一身接一身的汗,冷水一激,滞了(老家读chi,二声)。记得严塆有两起,后果很严重。
塆里的南征哥“挑草头”没穿蓑衣,没戴斗笠打科头,被瓢泼的阵头雨淋滞了,暴得大病。赤脚医生只能当疑难杂症,胡乱对付些药,病愈后,口齿不清,脑子慢了半拍。
发小、同学严国泉,读书聪明,论辈分我叫叔,也是刚干完农活,炽热的身子,跳进塆里下塘洗澡儿滞了的。回到家里,暴病一场,从此落下后遗症。拖了几年,终于在一个午后,自言自语说不愿拖累家人,转身喝药轻生,才二十出头。(此前说是病发,掉到厕所遇难,是讹传。)
身子滚热,毛孔大开,突遭冷水,暴冷暴热,毛孔关闭,一个“滞”字,应该恰当。
大热天的,在外喝井水,回家拿葫芦瓢在水缸里舀水喝,或者吃冷食,也怕滞了。要是小孩这样,大人的提醒、教训和责骂,就会说“滞了啊!”、“滞病了么办!?”
最是恐怖的,虽然不一定都发生在“双抢”期间,也不一定发生在严塆,但一定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而“双抢”期间,是多发。
农村人尤其是细伢,除了冬天,走路。干活多是赤脚。没有不被瓦片、石头、各种植物、螺蛳蚌壳和破铜烂铁割伤的,而且决不只一次。家里穷的,清水洗洗;懂一点常识的,化点盐水冲冲;家境好一点的,搽一点红汞(红药水)、紫药水。有碘酒的人家极少。
当年严塆人眼中的药,只红汞、紫药水两样。也不确切知道用法,有什么搽什么,胡乱地搽。经常可以看到身上搽的红红紫紫的怪异图案的孩子。
很久以后听说所谓“破伤风”“败血症”,有些后怕,也不以为然。
即便在80年代的浠水农村,悲剧照样发生。
我的一位好友,浠水县巴河人。80年代初读大学期间,就两次接到家里来人报信,一路痛哭回家。
先是快成年的弟弟,染上急性脑膜炎,无力救治,夭折。
接着是,妹妹在田里被蚌壳割伤,得了破伤风,不幸夭折。才14岁,正是豆蔻年华。
而他本人,在70年代末高考前夕,全身传染无名的水泡,同学怕被传染,自然嫌弃,于是休学。无力医治,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基本被家人放弃。他说好几次,在屋前的坪子晒太阳,斜躺在椅子上,预计着死亡的日子。
后来时走亲戚的姑妈,看不过眼,二话不说,带回家去,找些蝉蜕煮水,土方子救了这个侄子。
这家伙现在武汉大学做教授。
网上介绍,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侵入人体伤口后,在厌氧环境下生长繁殖,产生嗜神经外毒素而引起全身肌肉强直性痉挛为特点的急性传染病。重型患者可因喉痉挛或继发严重肺部感染而死亡。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推行了全球免疫计划,据估计全世界每年仍有近百万破伤风病例,数十万新生儿死于破伤风。
那个年代我听过的病,有急性脑膜炎、急性黄疸肝炎、急性肺炎、急性胃炎、急性支气管炎。还有疥疮,水泡,莫名其妙的过敏,不知原因的红、肿、热、痛。还有小孩子多见的出鼻血。
而疫苗,只有一种,叫“牛痘”。
药,是红汞、紫药水、人丹、十滴水。
医生,有大队赤脚医生杨大才等三个。
稀里糊涂活下来的,都是“幸存者”。
母亲每次自责,就发出“不晓得那么时候,你们五个伢是么样活的哦”的疑惑。
(泍田。就是沼泽)
四
打了小麦,打了谷,首先要交公粮。“双抢”割了早稻打完谷,也是。
用箩筐挑。男人一百多斤甚至接近两百斤一担,女劳力也百把斤一担。当年还叫三店公社,送粮就送到三店。送粮的路线,是严塆——老大队部——曙光小学——豹龙庙南——途径夏湾——三店,全程七八里路。
途径一个大畈,凹下去,来回要上下两个长坡。大路两旁,都是杨树。
我送过几年公粮到三店,挑的重量,略大于体重,从四五十斤逐渐升至到七八十斤。
交公粮,要挑好的,沤谷不行,沤谷分给社员吃。当年交小麦、油菜籽、落生儿、棉花、芝麻等等,都是这个标准。就想不通。
与此同时,一个问题,几乎困惑了我整个的少年时期——东西都是我们农民种的,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凭什么要给了城里人!
交完公粮,就是分口粮,分早稻谷,吃新米。我只记得分谷分小麦,地点在稻场,分苕、分柴,有时候就在地里分。
莲花儿表姐告诉我,当年的口粮是这样分的:
人均每月的标准是30斤谷。每个月1号发口粮,28斤。15号发工分粮,2斤。这2斤,叫“工分粮”,给“跑分”跑的多的人家,多做多吃。跑分,就是多做工分。
她还说,我舅家当年正在“打keba”,跑分总是跑不过别人,基本没有工分粮,分完粮后,总要到赶她家讨谷。从不让舅空手走。
浠水人说“打keba”,指的是家里孩子都未成年,缺劳力挣工分。
“keba”不知道应该是哪两个字。如是“磕巴”,有结结巴巴、紧紧巴巴的意思,“打磕巴”的说法很形象;写做“窠巴”,窠,有“空缺”意,喻缺少劳力,“打窠巴”似乎也贴切。
记得“双抢”后,是薅田,然后是割晚稻,然后是冬播,然后是过年,然后是“四快”(也要抢季节,所以叫“抢四快”)。具体准确的农时,具体种什么庄稼,记不完全准确。但都做过。
再然后,连接来年的“双抢”。
一年四季的“生糊”,几乎无缝衔接,转一个圈圈,终点又回到起点,没有尽头。
“双抢”记工分,与其他农时基本一样。按面积计,按早工、半天、整天、夜工计,按件计……应该有一套《打分规则》。
如按天打分,壮劳力,男人一天13分,女人10分。每个人,都是从八九岁开始,几厘几分地做上去的。
(箩筐和口粮)
五
当年情形的“双抢”,到现在全然不复当初。
80年代初在武汉读书,“双抢”时回了趟塆里,赶到小冲,找到正在插秧的堂妹严国容,还赤脚下田插了几行秧。其时“双抢”依旧,赤脚走在田埂上的我,也非当初,情绪复杂。
再往后,是包产到户,农民开始进城,自家的田地,开始被委托或租借亲朋好友代种,直至荒凉。
听说现在基本只种中稻一季。有的人只种晚稻(早二季稻)。也很少用牛,机器盘田,拖平,捞沟。也不再育秧、扯秧,直接撒谷种。虽然不成行,耗种子,也比插秧插得浅,但发窠(分蘖)还大些,产量高。但打农药多。
这几年时兴割谷后,留谷蔸,蓄秧芯儿。
秧芯儿,老家读起来像是“秧雀儿”。“蓄”作动词,本义是“聚集、储藏”。
蓄秧芯的方法,应该类似于古人的刀耕火种:割谷后,不盘田,不搞田间管理,不施化肥,打药极少,任由谷蔸子冲苗、抽穗、成熟,然后收割。
当年就听老人说,秧芯米十分好吃。但产量极低,蓄秧芯应该不被允许。而现在亩产竟有斤上下,打药又少,多是粳稻,加上生长期的气候原因,比其它稻米瓷妥一些。
蓄,老家还拿来讥讽懒人。不爱做事,不下田地做“生糊”,会被人讥讽或者责骂:“在屋里‘蓄到’撒!”
老家话“蓄”,读作“休”,二声。很多年后,我甚至觉得“修养”,其实是“蓄养”。
整个“双抢”期间,农村男女老少,没人找得到“蓄到”的借口和机会。
在畈里做“生糊”,歇气的时候,只能找个阴凉,坐在地上,半张着嘴,像狗一样喘。
(当年标准的“薅田照”。很珍贵。)
调“段距”,重发。别重复打赏!
赞赏
人赞赏
北京哪个医院看白癜风病最好北京白癜风治疗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