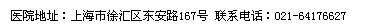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急性淋巴管炎 > 淋巴管炎用药 > B细胞血液恶性肿瘤的CART细胞疗法
B细胞血液恶性肿瘤的CART细胞疗法
摘要: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是一种过继性细胞疗法的创新形式,彻底改变了某些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包括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和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全部)。目前还在其他B细胞肿瘤中研究这种治疗方法,包括多发性骨髓瘤(MM)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LL)。CD19和B细胞成熟抗原(BCMA)已成为这些恶性肿瘤的CAR-T细胞免疫疗法最流行的靶抗原。这篇评论将讨论来自针对CD19和BCMA的CAR-T细胞的关键临床研究的功效和毒性数据分别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恶性肿瘤(NHL,ALL,CLL)和MM。
1、简介几十年来,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以全身化疗,放疗和干细胞移植为主导。最近,对这些恶性肿瘤的遗传和分子基础的新见识为靶向治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对患者免疫系统与癌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深入的了解导致了几种创新免疫治疗的发展。这些最近引起极大兴奋的基于免疫学的治疗策略之一是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1]。在某些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类型和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治疗中,这种类型的过继细胞疗法(ACT)已被证明是一项真正的突破,目前还在其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进行评估包括多发性骨髓瘤(MM)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LL)[1]。
利用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实际上,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alloSCT)的发展首先凸显了T细胞消除癌细胞的潜力。在这方面,Kolb等。研究表明,输注供体淋巴细胞可以诱导慢性髓样白血病(CML)复发患者的长期缓解[]。使用ACT,可以从患者或供体中收集免疫细胞,然后对其进行离体操作和/或扩增,然后重新注入患者体内[1]。ACT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患者中是否存在足够数量的效应细胞,这反过来又需要具有天然抗肿瘤识别能力或对T细胞进行工程改造以提供这种识别能力的前体[1]。因此,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几种策略来改善过继刺激细胞的肿瘤识别能力。新型受体(即CAR)的基因工程导致了分子的发展,这种分子既可以识别肿瘤细胞表面上存在的蛋白质,又可以提供T细胞的活化,增殖和记忆功能[]。CAR构建体是杂合分子;细胞外部分基于单克隆抗体的结构并负责表面抗原识别。这种识别以一种主要的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独立的方式发生。细胞内部分基于与一个或多个共刺激域结合的T细胞受体(TCR)的结构,从而可以将抗原识别转化为T细胞激活[]。
、CAR-T细胞设计通常,CAR由三个主要域组成:胞外域,跨膜域和内域。CAR的胞外域或细胞外部分通常由单链可变片段形式的抗体衍生的重链和轻链以及一个铰链区组成。它改变了受体的特异性,使其能够独立于MHC分子识别细胞表面的抗原。由于以下几个原因,CD19被最频繁地选择作为B-NHL,B-ALL和B-CLL的靶抗原:在这些恶性肿瘤中它频繁且高水平表达,相对于其他潜在靶标(如CD0),其表达范围更广,更高或CD,以及它对健康组织中B细胞谱系的限制。CAR构建体的跨膜结构域主要在稳定CAR中起作用,而胞内内结构域在抗原识别后提供激活T细胞的必要信号[]。
多年来,CAR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代CAR的设计与内源TCR复合体相似。在这些初始构建体中,细胞内成分通常由CDζ组成,该CDζ与细胞外抗原识别域相连,从而可以直接,独立于MHC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4]。重要的是,这些第一代设计不包括共刺激域,因此不提供完整T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结果,这些第一代CAR-T细胞更易于凋亡,并且体内扩增潜力有限,从而导致不良的细胞毒性[4]。在第二代CAR中添加共刺激性信号域(例如,CD8、4-1BB)导致改善的T细胞活化,增强的生存能力以及体内修饰的T细胞的更有效扩增[4,5]。这些第二代受体构成了当前批准的CAR-T细胞疗法的基础。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每种类型的共刺激域在CAR信号传导中都有特定的作用。例如,基于CD8的CAR-T细胞表现出更强的效应细胞功能,但持久性有限,而4-1BB趋向于将CAR-T细胞推向中央记忆表型,从而导致持久性改善[6,7]。第三代CAR-T细胞结合了两个共刺激域(例如CD8和4-1BB)的信号传导潜能。第四代CAR的抗肿瘤活性,包括重定向用于通用细胞因子介导的杀伤(TRUCKs)的T细胞,还可以通过其他遗传修饰,例如通过添加用于细胞因子分泌的转基因(例如IL-1)来进一步增强)[8,9]。
、CAR-T细胞的制造与管理尽管已经使用了同种异体CAR-T细胞,但CAR-T细胞的生产通常始于采用大剂量白细胞分离术从患者(自体)收集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图1)。然后将细胞转移到细胞处理设备中,并在其中装载CAR,通常是通过将它们与编码CAR的病毒载体一起孵育,然后将它们输入T细胞并引入CAR-RNA(图1)。然后将该CARRNA反转录为DNA,再重组为T细胞基因组,从而导致永久性CAR基因掺入。慢病毒和γ-逆转录病毒载体都已用于原代T细胞的CAR基因转导(图1)[10]。
图1.CD19+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中靶向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的概况)。通过白细胞去除术从患者体内收集T细胞(1),然后通过慢病毒或逆转录病毒转导()将CD19CAR基因加载到T细胞中,然后进行离体扩增()。然后将所得的CAR-T细胞通过静脉内(i.v.)输液回输给患者(4)。通常在CAR-T细胞输注之前进行淋巴去毒化疗,以促进体内CAR-T细胞的扩增和持久性。Axi-cel,tisa-cel和liso-cel是第二代CAR,其细胞内部分包含T细胞受体ζ链(CDζ)和共刺激(-CS)域(CD8或4-1BB)。细胞内部分通过跨膜结构域(-TM)与CAR的细胞外部分相连,而跨膜结构域(-TM)与CAR的细胞外部分由铰链和抗原识别域组成。这三个构建体带有不同的铰链(-H),但与抗原结合结构域共享相同的鼠源FMC6衍生的单链可变片段(scFv)。
然后将CAR基因修饰的T细胞离体扩增,并制成药物静脉输液产品。细胞通常以单次输注的形式给药。从白细胞清除术到CAR-T细胞给药的中位时间为4-5周,从转诊到输液的整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个月的时间[11]。因此,医生经常进行桥接化疗,以避免疾病的快速发展,并在CAR-T细胞生产期间维持患者的总体状况。输注CAR-T细胞之前通常进行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等淋巴结清扫术(LD)(图1)[1]。LD化疗减少了体内T细胞的数量,包括调节性T细胞,因此上调了细胞因子,例如IL-7和IL-15[1]。这些细胞因子促进T细胞扩增并增强CAR-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4、CAR-T细胞疗法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功效和毒性在过去的几年中,CAR-T细胞疗法迅速兴起,FDA已批准了5种CAR-T细胞药物。美国药品管理局(FDA),后来由欧洲药品管理局(EMA)负责治疗成人中某些B细胞NHL类型,以及儿童和年轻人中复发/难治性(r/r)B-ALL。除此之外,CART细胞疗法的潜力也正在其他B细胞肿瘤中探索,例如MM和B-CLL[1,8]。
4.1非霍奇金淋巴瘤B细胞NHL是最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是最常见的亚型。尽管治疗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DLBCL患者发展为化学难治性疾病。目前,约三分之二的新诊断为DLBCL的患者通过一线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泼尼松龙(CHOP)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可治愈[1]。适合患有r/rDLBCL的患者的二线治疗标准是抢救化疗,然后进行自体SCT(ASCT)。不幸的是,大约二分之一的患者在二线治疗后仍将保持难治性或复发[1]。复发/难治性DLBCL的预后不良。基于SCHOLAR-1研究的数据,该研究是一项多队列回顾性研究,涉及66例患者,汇总了两项III期研究(CORAL和LY.1)和两个观察性队列的数据,其中r/rDLBCL仅6.个月(95%CI:5.9-7.0个月)[14]。为了克服DLBCL中的这种化学断裂性,已经探索了几种新颖的治疗策略,包括CAR-T细胞治疗。几项早期的单中心研究表明,NHL患者CD19导向的CAR-T细胞疗法具有显着的抗淋巴瘤活性,并为设计三项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15,16]。
ZUMA-1试验的II期部分评估了难治性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轴突。在这项研究中,不允许桥接治疗,LD方案由环磷酰胺和氟达拉滨组成。该试验的患者分为两个队列:第一个队列-最大的队列-包括DLBCL患者,而第二个队列由转化性滤泡性淋巴瘤(TFL)和原发性纵隔B细胞淋巴瘤(PMBCL)组成[17,18]。与历史对照相比,ZUMA-1的主要终点是接受轴静脉注射后6个月以上的患者的总缓解率(ORR)(SCHOLAR-1[14])。总共招募了位患者,其中位接受了axi-cel。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至少对三线治疗无效,并且1%的患者在ASCT后1个月内复发。在该试验的最新报告中,中位随访7.1个月,ORR为8%,完全缓解(CR)率为58%[17]。与SCHOLAR-1相比,这代表了较高的CR率[14]。CR患者仍未达到中位缓解持续时间(95%CI:1.9个月,无法估计),这突出了对axi-cel的持久性[17]。表1[17,18]中提供了有关ZUMA-1中功效数据的更详细的概述。
JULIET试验是使用抗CD19CAR-T细胞产品tisa-cel对r/rB细胞NHL患者进行的II期多中心全球研究[19,0]。JULIET的主要资格标准包括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DLBCL,占治疗患者的80%,或TFL);约有一半的患者患有难治性疾病,至少接受过三项先前的疗法(其中49%的患者包括ASCT)。与ZUMA-1相比,使用了冷冻保存的单采血液分离术产品,并允许快速进展性疾病的患者接受桥接化疗[0]。总体而言,9%的患者接受了桥接化疗。LD化疗由环磷酰胺和氟达拉滨或苯达莫司汀组成。与ZUMA-1试验相似,试验的主要终点是ORR和CR发生率。共有例患者入组,例患者接受了tisa-cel输注。在9例可评估反应的患者中(至少随访个月),报告的ORR和CR率分别为5%和40%。表1显示了更多功效细节[19]。
基于ZUMA-1和JULIET的有希望的结果,美国FDA分别于年10月和年5月批准了axi-cel和tisa-cel用于某些r/rB细胞NHL亚型。几个月后,两家代理商也都获得了EMA的批准。随着axi-cel和tisa-cel的批准,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在实际临床实践中报告该疗法的疗效此外,有55%的人接受了桥接疗法,而ZUMA-1不允许这样做。Nastoupil等人[4]、Jacobson等[5]和其他人[6]等人报道了有关使用axi-cel的“真实世界”数据。。总体而言,在研究中有4%的患者不符合ZUMA-1的纳入标准。在94例白细胞去除患者中,实际有74例被注入。最佳ORR(81%)和CR(57%)比率与ZUMA-1中报告的比率相似(分别为8%和58%)。这从根本上证实了axi-cel在r/rB细胞NHL(包括DLBCL,TFL和PMBCL)中的功效可以在临床试验的严格资格标准之外进行复制[4-6]。
liso-cel的多中心TRANSCENDNHL研究是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的CD19CAR-T细胞研究。对44名患有各种r/rB细胞NHL类型(包括DLBCL,TFL,PMBCL,FLb级和其他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的患者进行了白细胞去除术[1-]。像在ZUMA-1和JULIET中一样,DLBCL是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大约三分之二的患者允许进行桥接治疗。环磷酰胺和氟达拉滨组合用于淋巴结清扫术。在该试验中,总共有94名患者接受了输液,但有5名患者接受了不合格产品。在56例可评估反应的患者中,最佳ORR和CR率分别为7%和5%[1]。PFS和OS数据显示在表1[1]中。
CAR-T细胞治疗后观察到的最常见的急性毒性是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的神经毒性综合症(ICANS,以前称为CAR-T细胞相关性脑病综合症(CRES)),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致命[7]。CRS是由于大量淋巴细胞的免疫激活而导致的细胞因子升高引起的。主要症状包括发烧,低血压和低氧血症[7]。CUM发生的中位时间为–天,ZUMA-1中为axi-cel[17,18],朱丽叶中为tisa-cel[19],TRANSCEND[1]中为liso-cel5天。近年来,已经发布了CRS统一分级的指南,其中美国移植和细胞治疗学会(ASTCT)的指南已成为最广泛采用的指南[8]。CRS的评分为1(轻微)至4(威胁生命)[8]。在ZUMA-1(axi-cel)[17,18],JULIET(tisa-cel)[19]和TRANSCEND(lisocel)[1]中,任何等级的CRS的发生率分别为9%,58%和4。分别为%(表)。≥级CRS的发生率分别为11%,%和%(表)。在Nastoupil等人的实际研究中,有7%的患者患有严重的CRS[4,6]。
白介素6(IL-6)被认为是CRS的主要介体[7]。这解释了为什么托珠单抗(一种阻断IL-6受体的治疗性抗体)已成为治疗中重度CRS的首选药物[8,9]。在大多数患者中,它会导致CRS症状立即逆转。重要的是,就ORR,CR率或反应的持久性而言,托珠单抗似乎并未影响CAR-T细胞疗法的疗效[9]。在ZUMA-1(axi-cel)[17,18],JULIET(tisa-cel)[19]和TRANSCEND(liso-cel)[1]中,托珠单抗的使用率分别为4%,14%和19%患者,分别(表)。在现实世界中,tocilizumab的使用频率更高(Nastoupil等人在使用axi-cel进行的研究中占6%的案例)[4-6]。直到最近,由于担心其对T细胞功能的抑制作用,仅在严重的CRS病例中使用皮质类固醇[9]。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皮质类固醇可以安全地用于治疗CAR-T细胞相关的毒性而不限制疗效。关于在r/rB细胞NHL中使用axi-cel的真实世界数据(即,在ZUMA-1和Nastoupil等人的真实世界研究中具有相似的功效,尽管比例更高)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说法。使用皮质类固醇治疗CRS(ZUMA-1中为55%,而ZUMA-1为7%)[4,6]。
神经毒性,称为ICANS或CRES,是施用CAR-T细胞疗法后的第二大最常见的严重不良反应[8]。受影响的患者发展为中毒性脑病,伴有精神错乱,失语,共济失调,癫痫发作和脑水肿[8]。这些神经系统副作用的病因病理生理仍未完全了解。IL-6在ICANS/CRES中似乎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在小鼠模型中,优美地显示了托珠单抗的抗IL-6治疗对ICANS/CRES的发生和发展没有重大影响[0]。尽管如此,仍会经常使用tocilizumab,特别是如果神经毒性与CRS同时发生时。否则,皮质类固醇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或者,如果有IL-1受体阻滞剂,则是首选治疗方法。ICANS的严重性可能会迅速波动,因此需要密切监控患者。这对于非常罕见但危及生命的脑水肿尤其重要,因为抗IL-6治疗无效[9]。类似于CRS,ICANS的管理基于神经系统症状的严重性。10点“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脑病(ICE)”评分工具现已成为筛选和分级ICANS的金标准[8]。与tisa-cel(1%的JULIET中1%≥级)和licel-cel(TRANSCEND[1]中0%且10%等级≥)相比,axi-cel(67%的ZUMA-1的%≥级的神经毒性)似乎更常见[19](表)。
4.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II期ELIANA试验研究了CD19定向基因修饰的自体T细胞产物tisa-cel作为r/r儿科和年轻成人B细胞ALL的单次输注[1]。在筛选出的位患者中,有9位入选;由于多种原因,有17名患者不能输液:死亡(N=7),严重不良事件(N=)或CAR-T细胞生产失败(N=7)。在75例接受tisa-cel治疗的患者中,有65例(87%)在入组与输液之间需要桥接化疗,而7例(96%)接受了LD化疗(主要是氟达拉滨加环磷酰胺)。该研究的患者接受了种先前疗法的中位治疗,之前接受过alloSCT的患者为61%.个月的CR率为81%,中位随访1年未达到中位缓解时间。所有具有治疗反应的患者的最小残留疾病(MRD)均为阴性。6个月的无事件生存率(EFS)和OS率分别为7%和90%,在1年的里程碑期下降至50%和76%[1]。证明了体内长期的持久性。所有对治疗有反应的患者均患有B细胞发育不全,并且该研究中的大多数患者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接受了免疫球蛋白替代。怀疑与tisa-cel相关的/4级不良事件(AEs)发生在7%的患者中。77%的患者发生了CRS,其中48%的患者接受了tocilizumab治疗。在40%的患者中观察到了神经毒性;所有这些事件都在头个月内发生[1]。Tisa-cel已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可用于治疗5岁以下顽固性B-ALL,在alloSCT后复发或第二次或以后复发的小儿和成年青年患者。
4.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是B细胞肿瘤,其特征在于骨髓中浆细胞的恶性增殖。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目睹了MM的巨大进步,但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该病仍无法治愈。因此,需要开发新的治疗药物,并且CAR-T细胞疗法被认为是有前途的。B细胞成熟抗原(BCMA)是MMCAR-T细胞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靶抗原[-4]。BCMA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恶性)浆细胞和一些成熟的B细胞[5,6]。BCMA似乎在促进MM细胞存活,增殖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还发现它与耐药性的发展有关[7]。表概述了在WebofScience/Pubmed上作为全文发表的所有MM中BCMACAR-T细胞临床试验(最新搜索日期:00年1月1日)[8-44]。由于大多数试验的早期特征,输注的患者数量很少。在大多数研究中,ORR的范围在85%至95%之间;只有两项研究NCT[8]和NCT[9,40]报告了较低的ORR和CR率。可能的解释是这些试验中使用的次佳BCMACAR-T细胞剂量不足,以及大多数患者接受了充分预处理的事实。BCMACAR-T细胞疗法观察到的中位PFS为1年[41-44]。如表所示,大多数患者发展为CRS。在5–41%的患者中观察到级或更高的CRS。神经毒性是罕见的事件,通常发生在不到10%的患者中。只有两项研究报告神经毒性发生率分别为%[8%]和4%[41]。
尽管用BCMACAR-T细胞疗法获得了相对较高的ORR,但观察到的治疗效果通常是短暂的,并且经常观察到复发。BCMA表达下调或丧失可能是这些复发的重要机制[45]。因此,在CAR-T细胞研究中已经研究了BCMA以外的靶标,例如CD19或CD18,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46,47]。例如,通过组合BCMA和CD19CAR-T细胞来实现双重抗原靶向也正在尝试中,以期提高应答的持久性[44]。CD19是MM中非常规的靶抗原,因为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骨髓瘤细胞大多为CD19阴性。然而,最近更敏感的技术表明CD19在MM细胞上以超低水平表达,这些水平足以被CD19CART细胞识别MM细胞[48]。此外,似乎CD19+MM细胞具有癌症干细胞的特征(即自我更新和耐药性),使其成为免疫疗法的诱人靶标[49]。避免BCMA阴性复发的另一种策略涉及将BCMACAR-T细胞与γ分泌酶抑制剂联合使用,以防止BCMA从MM细胞表面分裂[50]。除此之外,其他研究也在寻找针对其他抗原的CART细胞疗法的潜力,其中包括CD8,SLAMF7,CD44v6,CD56,GPRC5D等[51]。目前尚无监管机构批准用于MM的CAR-T细胞疗法,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或01年获得首批批准。
4.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CLL是最早检测CD19CAR-T细胞的疾病之一。自年首次报道第二代CAR-T细胞对抗CLL的疗效以来[5],已报道了以CD19为靶点的CAR-T细胞疗法在总共14名CLL患者中的结果[5]。总体而言,接受CAR-T细胞疗法治疗的CLL患者的预后特别差,其中大多数患者在接受大量治疗后复发。在这些研究中,总共名患者中有74名(68.5%)患有p5改变,而70名患者中有41名(58.6%)具有复杂的核型[5]。来自CLL的不同CAR-T细胞报告的第二个观察结果是,CLL的疗效低于DLBCL或B-ALL的功效:根据IWCLL标准,CR的疗效仅占少数(0-0%)估计18个月PFS为5%的患者[54-56]。有趣的是,在淋巴结中的反应似乎比在骨髓和血液中的反应弱。实际上,在某些系列中,接受CAR-T细胞治疗的患者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在骨髓中未检出MRD[55,57,58]。例如,在Turtle等人的研究中。包括4名先前曾接受过ibrutinib的CLL患者,CAR-T细胞输注四周后报告ORR为71%(CR为1%),而骨髓阴性率为58%。在这些MRD阴性患者中,中位随访6.6个月时,PFS和OS率几乎为%[55]。
CAR-T细胞在CLL中的疗效较低可能部分归因于CLL患者的T细胞衰竭,导致CAR-T细胞功能降低[59]。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几个研究小组正在研究优化CLL中CAR结构的方法。除此之外,正在进行的研究正在探讨将CAR-T细胞疗法与其他抗CLL疗法相结合的潜力。在这方面,数据表明,依鲁替尼可能会改善接受CAR-T细胞的CLL患者的预后[57,58]。基于这些观察,一项前瞻性研究将进一步评估注射CAR-T细胞(NCT98)时依鲁替尼维持的疗效。
5.结论和未来展望CAR-T细胞疗法正在成为r/rB细胞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补充[60]。在某些侵略性B细胞NHL亚型(包括DLBCL)中,以CD19为目标的CAR-T细胞疗法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临床活性。在NHL中使用的三种最先进的CD19CAR-T细胞产品是axi-cel,tisa-cel和liso-cel。总的CR率在50%的范围内,对于化学难治性DLBCL的患者,在先前的几种治疗方法中均无效[14],这的确的很高。
此外,这三种药物的PFS曲线在其尾部显示出平稳状态,表明在大约1/的NHL患者中可以观察到持久的反应[17,19]。然而,这种高效率是以实质毒性为代价的。根据本综述中的毒性数据(表),可以得出结论,liso-cel在严重CRS和神经毒性方面具有良好的安全性[1],但是否依赖于产物尚待确定[61]。在B-ALL中,tisa-cel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用于治疗5岁以下的r/rB-ALL的小儿和成年青年患者的CD19CAR-T细胞产品。
毒性是相当大的,但是由于这些患者可用的有效抢救治疗方法很少,因此被普遍接受[1]。r/rMM患者可以受益于针对BCMA的CAR-T细胞疗法。在选定的研究中,BCMACAR-T细胞在r/rMM中具有高活性,ORR率为85–95%(表),CR率高达80%[4]。中位PFS约为1个月,在经过大量预处理的MM患者中,这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毒性是常见的,据报道有75%的患者患有CRS。神经毒性的发生似乎是特定于产品的(表)。最后,在r/rB-CLL中,已经测试了CD19CAR-T细胞,但反应率却令人失望[54-56]。在这些患者中,可能需要与依鲁替尼联合使用的策略才能发挥CD19CAR-T细胞疗法的全部治疗潜力[6]。
关于功效,现在必须将重点放在改善反应的持久性上,从而也应着重于开发应对复发的策略。已经确定了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的两种主要机制,包括由于靶抗原丢失或下调引起的复发(抗原阴性复发)和由于CAR-T细胞的持久性和衰竭性较差引起的复发(因此,由于靶抗原仍保留在肿瘤细胞表面,因此称为抗原阳性复发[6]。抗原阴性复发可能是由于CAR-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压力所致,导致抗原阴性克隆或抗原表达降低的克隆的生长[64]。Fry等。率先确定使用靶向替代抗原CD的CAR-T细胞可以挽救CD19靶向CAR-T细胞治疗后经历抗原阴性复发的r/rB-ALL患者。这为克服抗原逃逸的双重抗原靶向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动力[66]。现在已经开始对CD19+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进行CD19和另一种抗原(如CD和CD0)联合靶向研究的几项早期CAR-T细胞临床试验[67,68]。同样,在MM中,已经公开了一种使用BCMA和CD19CAR-T细胞的双抗原方法[44],并且正在快速鉴定出新颖的MM抗原(例如GPRC5D),以便与BCMA进行合理的联合靶向[51,69]。]。在MM中,也可以通过结合使用BCMACAR-T细胞和γ-分泌酶抑制剂来阻止BCMA阴性复发,γ-分泌酶是负责从MM细胞表面主动裂解BCMA的酶[50]。
可以通过改善持久性和采取适当的抗疲惫措施来克服抗原阳性的复发。一种策略是使用比来自FMC6的scFv更快的CD19相互作用时间的低亲和力CD19CAR(CAT),FMC6是在axi-cel,tisa-cel和liso-cel(图1)。在一小部分儿科r/rB-ALL患者(n=14)中,使用这种具有持久性的CATCAR可以观察到CAR-T细胞持续性延长回应[70]。tonic信号传导,即在靶抗原不存在下触发组成型CAR,已被认为是导致CAR-T细胞衰竭的重要机制[9,71]。Long等的结果表明,共刺激域的选择对这种现象有影响,CD8增强和4-1BB减轻了tonicCAR信号后的CAR-T细胞衰竭[7]。对NHL患者中CD8和4-1BB共刺激的CD19CAR-T细胞进行成对直接比较,发现4-1BB变异可改善持久性,表明4-1BB共刺激有利于更持久的反应[7]。然而,在低CD19抗原密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CD8共刺激域,因为与它们的4-1BB对应物相比,CD8共刺激的CAR-T细胞在靶向低CD19的肿瘤细胞上更有效[7]。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来自无反应者或(早期)复发者的CAR-T细胞更容易衰竭,并显示出免疫检查点分子(例如PD-1)的表达增加[56,74]。从概念上讲,免疫检查点阻断可以帮助恢复这些疲惫的CAR-T细胞的功能,目前正在进行多项将CAR-T细胞与检查点抑制剂结合的研究[75-77]。为了避免全身施用的检查点抑制剂的毒性,还对CAR-T细胞进行了基因修饰,使其局部释放PD-1阻断抗体[78]。或者,也可以用c-Jun“装甲”CAR-T细胞以防止其耗尽[71]。
关于毒性,正在探索几种方法来改善CAR-T细胞疗法的整体安全性。当出现CRS的早期迹象时,现在正在使用Tocilizumab和皮质类固醇,从而降低了严重CRS的发生率[79]。其他策略涉及将自杀基因掺入CAR结构中,该毒性可在毒性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被激活[80]。同样,也可以修饰CAR-T细胞以共表达截短的(无活性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抗EGFRmAb西妥昔单抗的使用将在严重毒性的情况下选择性清除CAR-T细胞[80]。这些策略的缺点是它们导致CAR-T细胞的不可逆消除。最近,已证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达沙替尼可用作CAR-T细胞的药理“开/关”开关。它可以在撤药后立即恢复其功能并立即滴定抑制CAR-T细胞的功能[81]。或者,当使用编码CAR的mRNA瞬时修饰CAR-T细胞时,潜在的毒性将是自限性的[8],这使得该方法对于评估新型CAR构建物的安全性特别有用。
尽管在功效水平,尤其是在改善反应持久性和毒性水平方面仍然存在这些挑战,但很显然,CAR-T细胞疗法在这里仍将是r/r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的一种重要治疗方式。
原文来源:doi:10.90/pharmaceutics194识别